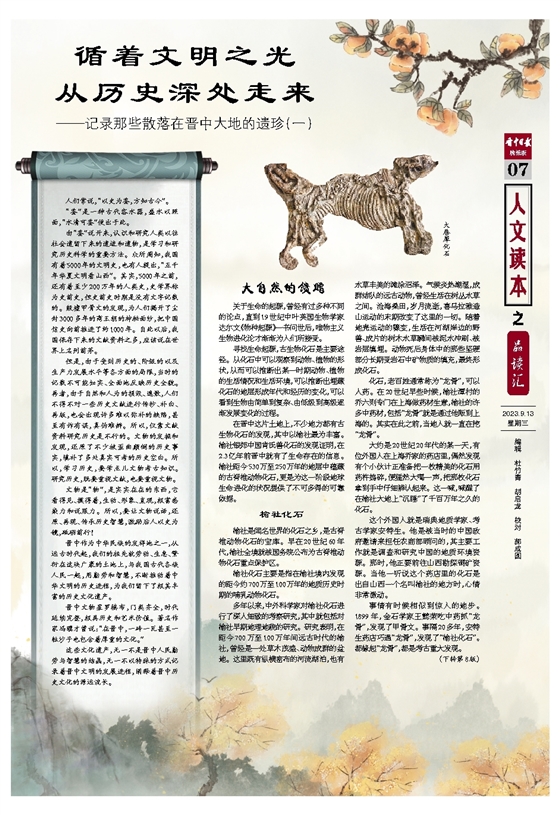循着文明之光 从历史深处走来
——记录那些散落在晋中大地的遗珍(一)
人们常说,“以史为鉴,方知古今”。
“鉴”是一种古代容水器,盛水以照面,“水清可鉴”便出于此。
由“鉴”说开来,认识和研究人类以往社会遗留下来的遗迹和遗物,是学习和研究历史科学的重要方法。众所周知,我国有着5000年的文明史,也有人提出,“五千年华夏文明看山西”。其实,5000年之前,还有着至少200万年的人类史,史学界称为史前史,但史前史时期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为人们揭开了尘封3000多年的商王朝的神秘面纱,把中国信史向前推进了约1000年。自此以后,我国保存下来的文献资料之多,应该说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但是,由于受到历史的、阶级的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各方面的局限,当时的记载不可能如实、全面地反映历史全貌。再者,由于自然和人为的损毁、逸散,人们不得不对一些历史文献进行传抄、补白、再版,也会出现许多难以弥补的缺陷,甚至有诈有误,真伪难辨。所以,仅靠文献资料研究历史是不行的。文物的发掘和发现,还原了不少被歪曲颠倒的历史事实,填补了多处真实可考的历史空白。所以,学习历史,要学点儿文物考古知识。研究历史,既要重视文献,也要重视文物。
文物是“物”,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它看得见、摸得着,生动、形象、直观,极富感染力和说服力。所以,要让文物说话,还原、再现、传承历史智慧,激励后人以史为镜,砥砺前行!
晋中作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从远古时代起,我们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与我国古代各族人民一起,用勤劳和智慧,不断推动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为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晋中文物星罗棋布,门类齐全,时代延续完整,极具历史和艺术价值。著名作家冯骥才曾说:“在晋中,一砖一瓦甚至一粒沙子也包含着厚重的文化。”
这些文化遗产,无一不是晋中人民勤劳与智慧的结晶,无一不以特殊的方式记录着晋中文明的发展进程,阐释着晋中历史文化的源远流长。
大自然的馈赠
关于生命的起源,曾经有过多种不同的论点,直到19世纪中叶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后,唯物主义生物进化论才渐渐为人们所接受。
寻找生命起源,古生物化石是主要途径。从化石中可以观察到动物、植物的形状,从而可以推断出某一时期动物、植物的生活情况和生活环境,可以推断出埋藏化石的地层形成年代和经历的变化,可以看到生物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逐渐发展变化的过程。
在晋中这片土地上,不少地方都有古生物化石的发现,其中以榆社最为丰富。榆社银郊中国肯氏兽化石的发现证明,在2.3亿年前晋中就有了生命存在的信息。榆社距今530万至250万年的地层中蕴藏的古脊椎动物化石,更是为这一阶段地球生命进化的状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可靠依据。
榆社化石
榆社是闻名世界的化石之乡,是古脊椎动物化石的宝库。早在20世纪60年代,榆社全境就被国务院公布为古脊椎动物化石重点保护区。
榆社化石主要是指在榆社境内发现的距今约700万至100万年的地质历史时期的哺乳动物化石。
多年以来,中外科学家对榆社化石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研究,其中就包括对榆社早期地理地貌的研究。研究表明,在距今700万至100万年间远古时代的榆社,曾经是一处草木茂盛、动物成群的盆地。这里既有纵横密布的河流湖泊,也有水草丰美的滩涂沼泽。气候炎热潮湿,成群结队的远古动物,曾经生活在树丛水草之间。沧海桑田,岁月流逝,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末期改变了这里的一切。随着地壳运动的骤变,生活在河湖岸边的野兽、成片的树木水草瞬间被泥水冲刷、被岩层填埋。动物死后身体中的那些坚硬部分长期受岩石中矿物质的填充,最终形成化石。
化石,老百姓通常称为“龙骨”,可以入药。在20世纪早些时候,榆社潭村的乔六则专门在上海做药材生意,榆社的许多中药材,包括“龙骨”就是通过他贩到上海的。其实在此之前,当地人就一直在挖“龙骨”。
大约是20世纪20年代的某一天,有位外国人在上海乔家的药店里,偶然发现有个小伙计正准备把一枚精美的化石用药杵捣碎,便猛然大喝一声,把那枚化石拿到手中仔细辨认起来。这一喊,喊醒了在榆社大地上“沉睡”了千百万年之久的化石。
这个外国人就是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他是被当时的中国政府邀请来担任农商部顾问的,其主要工作就是调查和研究中国的地质环境资源。那时,他正要前往山西勘探铜矿资源。当他一听说这个药店里的化石是出自山西一个名叫榆社的地方时,心情非常激动。
事情有时候相似到惊人的地步。1899 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吃中药抓“龙骨”,发现了甲骨文。事隔20多年,安特生药店巧遇“龙骨”,发现了“榆社化石”。都缘起“龙骨”,都是考古重大发现。
1931 年,工作繁忙的安特生特意派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技工刘师固来榆社考察化石。刘师固来到榆社,发现榆社哺乳动物化石非常丰富。消息传回,安特生兴奋不已,并很快把这个消息传递给了地质古生物界的朋友们。于是,许多地质古生物学家、古人类学家纷至沓来。这些人中,最著名的有法国昆虫专家桑志华、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和中国最早的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汤平道等人。他们把采集到的成千上万件化石标本整理装箱运往天津,收藏在那里的黄河白河博物馆(天津自然博物馆前身)。直至1938年桑志华离开中国时,已收集或发掘到2000多件榆社化石标本,大多是具有极高研究价值的哺乳动物头骨、牙齿、角等部位。而后,美国人福莱德专门雇用了瑞典人新常富在榆社收集了十余年化石。所收集化石除一部分留在天津黄河白河博物馆外,大部分通过天津口岸运往欧美。至今,天津黄河白河博物馆收藏有榆社化石标本1000多件。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中保存有2000余件珍贵的榆社化石。法国巴黎自然博物馆、英国伦敦自然博物馆等国外博物馆中也有榆社出土的化石标本。
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和研究机构非常重视榆社化石的保护和研究。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地质博物馆等科研单位和收藏展示单位先后到榆社进行考察发掘。1956年,苏联古生物学家访华代表团在中国科学院教授裴文中、周明镇的陪同下到榆社进行科学考察活动。1961年,国务院公布榆社全境为“古脊椎动物化石”重点保护区。
改革开放以来,榆社化石迎来了新一轮的考察研究高潮。国内外许多科研机构和收藏展示单位对榆社盆地进行了古地磁采样、测量地层剖面、大哺乳动物化石核对层位、小哺乳动物化石筛选,以及榆社盆地的形成等多学科的信息采集和深入研究,发表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专著。
目前出土的榆社化石共有7个目、17个科。主要有鱼、陆龟、鬣狗、猞猁、剑齿虎、丁氏貉、山西轴麂、原额中华大羚等。以榆社地名命名的有:榆社鲴、榆社狐、榆社剑齿象、云簇额鼻角犀、银郊中国肯氏兽等。
榆社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化石为距今530万年至250万年间的化石。因为这一地质时期的化石在全世界来说还是个缺环,恰好榆社化石填补了这一空白,衔接了生物进化演变的链条。正如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专家邓涛所言:“这一发现,奠定了榆社化石在研究古代环境演变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所以,它在学术上具有“唯一性”“不可替代性”和“承上启下性”。也正因为如此,榆社成为闻名中外的“化石之乡”和“古脊椎动物化石宝库”,并借此获得了“远古地球生命信息库”的美誉。
远古钩沉
有了人,就有了历史。
人们一般将文字出现以前的人类历史称为史前史,将史前社会形态称为原始社会。考古学家又按照人类使用生产工具的性质把史前史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个阶段。旧石器是指以打制方法制作的石器,新石器是指磨制的石器。
考古学家把旧石器时代分为早、中、晚三期。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生活在距今大约200万年至15万年;到距今15万年至5万年,进入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5万年至1万年进入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
山西是古代人类的起源地之一。有资料表明,山西境内已发现了旧石器地点300余处,是探索中国早期人类历史的重要区域。晋中范围内目前已发现旧石器地点21处,这些地点主要分布在榆次、寿阳、昔阳、和顺、榆社等东部山区,是山西旧石器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探索这一地区的人类起源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历史信息。
十五万年前的劳动工具
探索晋中人类历史的渊源,进行考古研究是最有效的途径。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是人类进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所以,寻找人类化石和劳动工具就成了考古学家解开人类起源秘密的一把金钥匙。
20世纪50年代初,晋中迎来了一队科学家,他们拿着小锤子、小铲子,这儿敲敲、那儿挖挖,似乎在寻找着什么。他们有时候捡起刨出的石块,有时候捡起“瓦渣片”,左看看、右瞧瞧,还不时地讨论、研究着什么,引得当地老乡们驻足观看。其实,他们是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文物普查队,正在进行全国第一次文物大普查。带队的正是旧石器时代考古专家王择义。
他们沿着浊漳河来到榆社盆地时,不禁被眼前的景象迷住了。只见清澈的浊漳河水自北而南从榆社城西流过,河边绿草茵茵,树木成荫。不远处的丘陵上、沟壑里,绿油油的庄稼漫山遍野,舒适、静谧的田园风情一望便知是非常适宜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再加上这里经常出土古脊椎动物化石,很有希望找到远古人类的遗迹和遗物。
他们到沟壑的断崖处踏勘,因为断崖处最容易暴露出历史时期的文化堆积。当他们走到墩圪塔、上西山、下西山一带时,断崖处时不时暴露出一些古脊椎动物化石。经验告诉他们,这一区域应该重点调查。果然,他们在这三个地点都采集到了一些人工打制的石制品。
这些石制品发现于红色土层中。红色土层底下是深红色黏土,上边是黄土。石制品的原料都是石英石。他们把这些石制品进行了分类研究,没有经过加工使用的石制品只能称为石片,经过加工使用的石制品才能称为石器。他们最后确认,经过加工并有使用痕迹的只有一件刮削器。这件刮削器并不算大,形似直角三角形,但加工痕迹和使用痕迹都很明显。
科学家们远眺榆社盆地的地形地貌,再端详手中的这些石制品,复原着15万年前这里的情景。
15万年前,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已经停止,经过剧烈造山运动的榆社盆地,地形地貌已经和今天基本一致。这里湖泊萎缩,纵横交错的河道逐渐形成,经过冰期的洗礼,气温逐渐回升,温暖湿润,草本植物繁盛,很适宜人类繁衍生息。
一个不大的人类原始群体在这里过着采集渔猎的生活。白天,他们三五成群,到野外捕食动物。遇有凶禽猛兽时,则需要更多的人进行围捕。除了猎捕动物外,他们还会到树木林草中采集野果。为了获得更多食物,他们最早使用了木棍去追打围攻动物,去摘打树上的果实。然后用石块砸击动物,敲开坚硬的果核。这便产生了木器和石器。木器容易腐朽,石器却保存了下来。
他们的脑容量已经和现代人差不多,把石块敲打成不同用途的石器,显示了原始人类的智慧。他们首先选择一块较大的有边有沿有平面的自然岩石,然后在平面近沿处打下石片。一层层、一块块地打,对打下的石片再进行加工。为了便于切割和刮净兽皮,他们把石片打成刃状,有的凹进去,有的凸出来;为了在木头、骨头或者兽皮上钻孔,他们又把石片加工成尖尖的锥、钻形状;为了便于更有力地获取动植物,他们把石块加工成能砍能砸的砍砸器。打来打去,这块石头打到最后,剩下的石核还可以进行投掷。
暑往寒来,他们把兽皮或树皮刮干净后,钻上孔连接在一起、遮盖在身上。不远处是他们居住的岩棚式山洞,自然形成的山洞冬避寒夏避暑,还可以遮风避雨,躲避猛兽的袭扰。当夜幕降临,人们取出火种,点燃篝火,一边烧烤着打猎捕获的动物,一边欢乐地唱歌、跳舞……
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专程到榆社考察了这里的地层和石制品。他认为,石制品虽然不能作出时代上的判断,但根据对地层的观察,应归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范畴中,下限最早不超过丁村,上限最迟也不晚于萨拉乌苏河(内蒙古),约与黄土底部砾石层的时代相当。
换句话说,至少从目前所获得的考古资料来看,晋中人类的历史应该从榆社写起,应该从15万年前写起。
五万年前的旧石器遗迹
20世纪50年代,文物工作者在寿阳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几处遗迹。
这几处遗迹分布在寿阳和阳泉的交界处,分别是寿阳的高垴、尹家庄、翚山和阳泉的枣烟、大梁丁。
这里黄土覆盖,沟壑纵横,已经被切割得支离破碎,植被不是很好。这几处遗迹的地层剖面构成相同,石制品都发现在黄土与红土交接的地层中,也就是地质学上说的更新世晚期马兰黄土层的底部。地质年代约与黄土底部砾石层的时代相当,为距今15万年至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中期。
石制品的原料岩性以燧石和石英岩居多。石核石器有大型砍砸器和小型刮削器,石片石器有刮削器和三角形背面加工的尖状器。刮削器较为丰富。
尽管寿阳这三处旧石器中期地点仅仅是初步发现,没有进一步的调查和发掘,但地质年代和文化分期十分清晰,在晋中旧石器时代文化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人类是在自然环境的长期演变过程中产生的,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距今14.5万年至1万年,地质学称为晚更新世,在地层上包括马兰黄土和第一层古土壤,相当于考古学旧石器时代的中期和晚期。
考古资料表明,晚更新世的早一阶段,距今约7.5万年以前,山西大地上生存着野马、披毛犀、野驴、原始牛、河套扁角鹿、貉等哺乳动物。当时在森林里有狼、貉、狐、熊、獾、野猪、印度象等;草原上奔跑着野马、野驴、披毛犀、羚羊等;而葛氏斑鹿、河狸、水牛等既能适应森林又能适应草原,有的在河湖沼泽里生活。
与这些古脊椎动物相伴的还有蚌科、蚬科、间齿螺、凸圆盘螺和一些鱼类,如青鱼等。
这时候山西境内的许多古湖泊、沼泽地尚未消失,他们就在这些古河边或湖滨生活着。当时,河湖沼泽中生长着香蒲、黑三棱、泽泻等水生植物,大片的草原上则繁生着蒿、藜为主的旱生草本或旱中生草本植物。在海拔较高的地方生长着许多落叶阔叶树种,如栎、榆、臭椿、桦、木樨、鹅耳枥等。北部植被主要是以云杉为主的暗针叶林和以蒿、藜为主的干草原。
这些植物和动物告诉我们,这个时期山西南北部的气候已经有所差别:南部温热并略干一些,比现在的气候还要暖和;北部夏季温暖,冬季寒冷,春秋两季凉爽宜人。哺乳动物中的披毛犀、鸵鸟等的存在很可能与季节性迁徙有关。晋中位于山西高原中部,自然环境差别不大,是南北间过渡性气候。寿阳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地点,说明这个时候晋中的古气候及其所处的生态环境是比较宜人的。
三万年前的人类化石
1983年的春夏之交,人们在和顺、左权的山沟里、溪水旁,经常能够看到一位年过半百的学者,他就是晋中地区文物工作站的吴志清。
吴志清原来是一位中学教师,在长年累月的教学生涯中,对中国古代史很是熟悉。学生们在他的熏陶下,对“古人类”“石器”“陶器”“化石”这些基本常识都有了初步的了解。一天,一个学生拿着一块化石让他看:“老师,这是不是化石?”“是化石,你从哪里捡回来的?”学生告诉他在榆次长凝村附近可以捡到。这块古生物化石激发了他寻找人类起源的梦想。他想,榆次长凝和北京基本处于相同的纬度,地形地貌也大致相同,北京可以发现北京猿人,榆次为什么不能发现呢?他要追寻人类的“足迹”,他要追寻自己的梦想。从此,他跑遍了榆次长凝附近的山山水水,先后在这里发现了贾鱼沟地点、大发地点等几处旧石器晚期人类活动的“足迹”。地质部门根据他发现地层的完整性和特殊性,把这里的地层剖面命名为“长凝组”。这些成果的取得,激起了他寻找古人类的兴趣,也引起了上级有关部门的注意。后来,他被调到了晋中地区文物工作站工作。
这次吴志清的左权、和顺之行,能否有所发现呢?
一般古人类的活动地点都会选择在河流两旁的二级台地上。河流两旁离水近,取水比较容易,而且在台地上,又可以躲避山洪突发,保障自身安全。
不虚此行,吴志清在和顺县青城镇当城村附近发现了一处洞穴遗址群。这些洞穴在前当城村西1公里,和(顺)邢(台)公路由洞口前穿过。这些洞穴大致可以分为上下两层,下面一层高出现代河床5米至7米,上面一层高出现代河床60米至80米,其中5处含有文化遗址的洞穴均属下层洞。下层洞中背窑湾洞文化层保存较为完整,文化遗物比较丰富。
背窑湾洞洞口向北,高出河床约5米,大致相当于河流第一级阶地。洞呈袋状,高7米,宽20.8米,深13.25米。经采集和试掘,洞内出土了2块人类顶骨化石,哺乳动物化石100余件,破碎骨片3000余件,还有石制品3200余件。另外还有新石器时代的磨光石斧和红陶片。石制品的原料绝大部分来自遗址以西3公里虎峪村附近的变质岩分布区。经过人工加工的类型有石核、石锤、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制作技术娴熟,加工细致。
洞内与石器一起被发现的还有两块人类顶骨化石,面积分别为2厘米×4厘米、2.2厘米×2.9厘米,厚约0.6厘米。
除人类化石外,还有刺猬、鼢鼠、兔、旱獭、最后斑鬣狗、熊、大角鹿、东北麅、羚羊、鹅喉羚等24种哺乳动物化石。
其实,人类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就开始使用骨器了。背窑湾洞穴遗址出土这么多的骨制品,真是耐人寻味。它至少可以告诉我们,骨器和石器一样,都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产、生活工具。
背窑湾洞穴遗址经过科学测定,距今3万年左右,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昔阳虎窑洞洞穴遗址
有些考古发现是在不经意间,有些考古发现则源于执着的追求。昔阳虎窑洞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址的发现,即属于后者。
1985年秋到1987年春,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正紧张有序地进行着。队员们骑着自行车,顶酷暑冒严寒,奔波在野外,宿营在山庄窝铺,渴了喝一口河水,饿了吃一块干粮,实在累得不行了,和衣就地一躺,铺大地盖蓝天,睡一会儿马上就走。近两年的时间,他们跑遍了晋中大地的山山水水、沟沟岔岔,登记不可移动文物4100多处。
由晋中地区文物工作站晋华带队的文物普查队在昔阳普查时,听老乡说河上村对面的山上有唐代的石碑,大家一听都来了兴趣,一鼓作气跑上山,一边擦着脸上的汗水,一边四处张望,搜寻那块“唐碑”。经仔细踏勘寻找,结果却一无所获。这时天近黄昏,众人连忙下山准备宿营。
就在大家刚下到山底准备返村时,队长晋华看到了一个山洞。他招呼大家说:“我们进去看看,说不定有化石,有旧石器。”有人说:“不可能吧,今天太累了,回吧。”晋华说:“不行,有怀疑咱们就得进去看看,明天就不一定过来了。”说着,他第一个进了洞,拿起手中的小铲刨了起来。不一会儿,他手里拿着几块化石。“这是什么?这不是动物化石吗?有化石就可能有古人类的遗物。”大家惊诧不已。当晚,人们住在了河上村小学的教室里,几张课桌拼在一起,“幸福”地睡了一晚。这种幸福是别人体会不到的。
时隔两个月,晋华、昔阳县文管所的翟盛荣、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陈哲英等人共同发掘了虎窑洞。
河上虎窑洞在阎庄乡河上村东南约2公里,是一个石灰岩洞。洞口东南向,高约15米,宽约14米,洞深11米,洞底宽不足3米,口大底小,近“V”形。杨照河由东向西北直冲洞口而来,然后弯弯曲曲流入松溪河。洞内的堆积相当于杨照河第一级阶地的后缘,厚约2米,在上部60厘米的文化层中,发现了石制品39件和少量的哺乳动物化石。
石制品原料岩性以脉石英为主,石英砂岩、水晶、燧石不多。器形有石核、石片、石锥、刮削器等。与这些石制品一起出土的还有少量的哺乳动物化石,有披毛犀、鹿和盘羊。这几种动物都是我国北方地质时代更新世晚期的常见动物。由此推断,虎窑洞内的文化层也是在更新世晚期形成的。
虎窑洞内出土的石制品虽然不多,石料也不太理想,但加工很精致,说明当时的制作技术已经达到了十分娴熟的地步。它的文化属性应该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与和顺背窑湾洞穴遗址大体相当。
榆次大发遗址
生命产生于水、依赖于水、繁盛于水。晋中城区南面有一条河,古名洞涡水,今称潇河。潇河发源于昔阳县,由东向西流经寿阳县、榆次区,又向西经太原市清徐县,注入汾河。
潇河岸边有一个小小的村落,叫大发村。这里冬季寒冷干燥,夏季却经常会有暴雨来袭。特别是七八月份,上游暴雨造成的洪水,会裹挟着大量泥沙、石块和植物、动物的碎片、残骸冲击到这里,在周而复始的过程中慢慢沉积,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历史的记忆。
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偶然的机会,吴志清从修路工人处听说他们在挖掘路基时发现了许多特殊的石块,便在工人的指引下来到了这个小村落,并在周围进行考古调查。
果然,在距大发村不远的潇河北岸,发现了一处旧石器地点。1988年至1990年,山西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先后两次对这一地点进行发掘。在此以前,吴志清也对大发地点进行过发掘清理。这几次发掘,在距地表3.5米至4.2米的灰白色砾砂层中,获得石制品近2000件,还有哺乳动物化石以及大量人工敲击的碎骨片。
石制品的原料岩性主要为燧石和石英岩,也有少量的角质岩、脉石英、硅质岩类和玛瑙。经过人工加工的类型有石核、石片和石器三大类。石核又可分为锤击石核、砸击石核和细石核,其形状分别呈锥状、楔状和柱状。石片是大发地点石制品的主体,类型包括锤击石片、砸击石片和石叶。石器由刮削器、尖状器和雕刻器组成。
大发遗址与石器一起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有:普氏野马、狼、蒙古野驴、大角鹿、披毛犀、普氏羚羊等。这些哺乳动物都是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地质年代中更新世晚期的常见种类,代表偏冷的气候环境和比较干燥的草原环境。大发遗址的地质年代为晚更新世晚期,文化时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大约距今2万年,是一处传统小石器和细石器并存的文化遗址。
本期人文读本摘选自晋中历史文化丛书·文物卷《沧海遗珍》,由本报编辑杜竹青整理,配图均为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