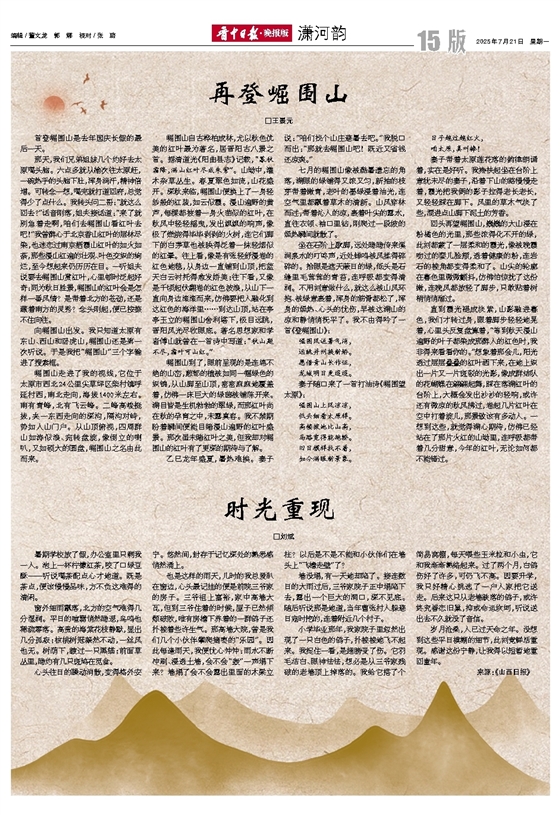再登崛围山
□王景元
首登崛围山是去年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
那天,我们兄弟姐妹几个约好去太原喝头脑。六点多就从榆次往太原赶,一碗热乎的头脑下肚,浑身淌汗,精神倍增。可转念一想,喝完就打道回府,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我转头问二哥:“就这么回去?”话音刚落,姐夫接话道:“来了就别急着走啊,咱们去崛围山看红叶去吧!”我曾醉心于北京香山红叶的层林尽染,也迷恋过南京栖霞山红叶的如火如荼,那些漫山红遍的壮观、叶色交织的绚烂,至今想起来仍历历在目。一听姐夫说要去崛围山赏红叶,心里顿时泛起好奇:同为秋日胜景,崛围山的红叶会是怎样一番风情?是带着北方的苍劲,还是藏着南方的灵秀?念头刚起,便已按捺不住向往。
向崛围山出发。我只知道太原有东山、西山和卧虎山,崛围山还是第一次听说。于是我把“崛围山”三个字输进了搜索框。
崛围山走进了我的视线,它位于太原市西北24公里尖草坪区柴村镇呼延村西,南北走向,海拔1400米左右。南有青峰,北有飞云峰。二峰高峻挺拔,夹一东西走向的深沟,隔沟对峙,势如入山门户。从山顶俯视,四周群山如涛似浪、宛转盘旋,像倒立的喇叭,又如硕大的圆盘,崛围山之名由此而来。
崛围山自古桦柏成林,尤以秋色优美的红叶最为著名,居晋阳古八景之首。据清道光《阳曲县志》记载,“暮秋霜降,满山红叶尽成朱紫”。山坳中,灌木杂草丛生。春夏翠色如流,山花盛开。深秋来临,崛围山便换上了一身轻纱般的红装,如云似霞。漫山遍野的黄芦,每棵都披着一身火苗似的红叶,在秋风中轻轻摇曳,发出飒飒的响声,像极了燃烧得毕毕剥剥的火树,连它们脚下的白茅草也被映得泛着一抹轻烟似的红晕。往上看,像是有张轻舒漫卷的红色地毯,从身边一直铺到山顶,把蓝天白云衬托得愈发娇美;往下看,又像是千顷起伏翻卷的红色波浪,从山下一直向身边滚滚而来,仿佛要把人融化到这红色的海洋里……到达山顶,站在亭亭玉立的崛围山舍利塔下,极目远眺,晋阳风光尽收眼底。著名思想家和学者傅山就曾在一首诗中写道:“秋山题不尽,霜叶可山红。”
崛围山到了,眼前呈现的是连绵不绝的山峦,葱郁的植被如同一幅绿色的织锦,从山脚至山顶,密密麻麻地覆盖着,仿佛一床巨大的绿茵被铺陈开来。满目皆是生机勃勃的翠绿,而那红叶尚在秋的孕育之中,未露真容。我不禁期盼着瞬间便能目睹漫山遍野的红叶盛景。那次虽未睹红叶之美,但我却对崛围山的红叶有了更深的期待与了解。
乙巳龙年盛夏,暑热难挨。妻子说:“咱们找个山庄避暑去吧。”我脱口而出:“那就去崛围山吧!既近又省钱还凉爽。”
七月的崛围山像被酷暑遗忘的角落,满眼的绿铺得又浓又匀,新抽的枝芽带着嫩青,老叶的墨绿浸着油光,连空气里都飘着草木的清新。山风穿林而过,带着沁人的凉,裹着叶尖的露水,直往衣领、袖口里钻,刚爬过一段坡的燥热瞬间就散了。
坐在石阶上歇脚,远处隐隐传来溪涧泉水的叮咚声,近处蝉鸣被风揉得碎碎的。抬眼是遮天蔽日的绿,低头是石缝里毛茸茸的青苔,连呼吸都变得清润。不用刻意做什么,就这么被山风环抱、被绿意裹着,浑身的筋骨都松了,浑身的燥热、心头的忧伤,早被这满山的凉和静悄悄抚平了。我不由得吟了一首《登崛围山》:
崛围风送暑气消,
远眺并州换新娇。
愿借青山长作证,
龙城明日更迢迢。
妻子随口来了一首打油诗《崛围望太原》:
崛围山上风凉凉,
低头细看太原样。
高楼拔地比山高,
马路宽得能跑轿。
旧日模样找不着,
如今满眼新景象。
日子越过越红火,
咱太原,真叫棒!
妻子带着太原莲花落的韵律朗诵着,实在是好听。我搀扶起坐在台阶上意犹未尽的妻子,沿着下山的路慢慢走着,霞光把我俩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又轻轻踩在脚下。风里的草木气淡了些,混进点山脚下泥土的芳香。
回头再望崛围山,巍巍的大山浸在粉橘色的光里,那些浓得化不开的绿,此刻都蒙了一层柔和的霞光,像被晚霞吻过的婴儿脸颊,透着健康的粉,连岩石的棱角都变得柔和了。山尖的轮廓在暮色里微微颤抖,仿佛怕惊扰了这份嫩,连晚风都放轻了脚步,只敢贴着树梢悄悄溜过。
直到霞光褪成淡紫,山影融进暮色,我们才转过身,跟着脚步轻轻地晃着,心里头反复盘算着,“等到秋天漫山遍野的叶子都染成那醉人的红色时,我非得来看看你的。”想象着那会儿,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红叶洒下来,在地上织出一片又一片斑驳的光影,像成群结队的花蝴蝶在翩翩起舞,踩在落满红叶的台阶上,大概会发出沙沙的轻响,或许还有微凉的秋风拂过,卷起几片红叶在空中打着旋儿,那景致该有多动人。一想到这些,就觉得满心期待,仿佛已经站在了那片火红的山坳里,连呼吸都带着几分甜意,今年的红叶,无论如何都不能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