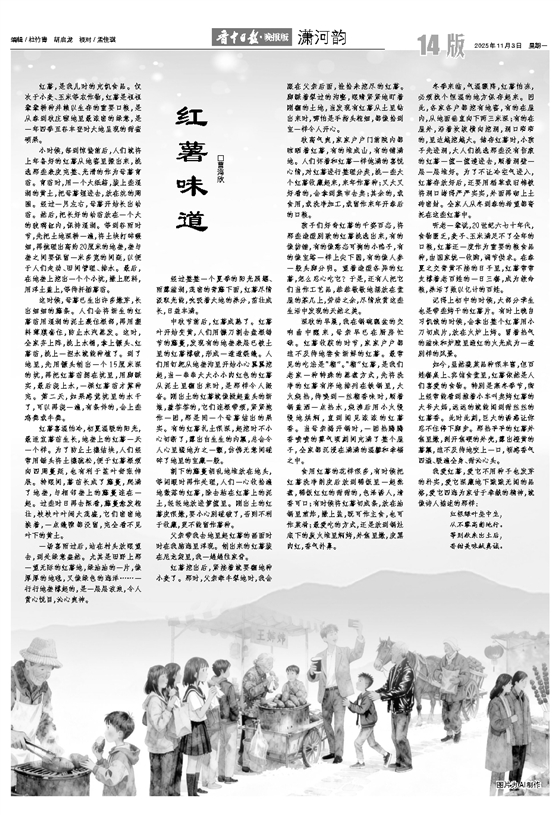红薯味道
□曹海欣
红薯,是我儿时的充饥食品。仅次于小麦、玉米等农作物,红薯是祖祖辈辈耕种并赖以生存的重要口粮,是从春到秋庄稼地里最浓密的绿意,是一年四季五谷丰登时大地呈现的甜蜜硕果。
小时候,每到惊蛰前后,人们就将上年备好的红薯从地窖里搬出来,挑选那些表皮完整、光滑的作为母薯育苗。育苗时,用一个大纸箱,装上些湿润的黄土,把母薯埋进去,放在炕的周围。经过一月左右,母薯开始长出幼苗。然后,把长好的幼苗放在一个大的玻璃缸内,保持湿润。等到谷雨时节,先把土地深耕一遍,将土块打碎碾细,再梳理出高约20厘米的地垄,垄与垄之间要保留一米多宽的间距,以便于人们走动、田间管理、排水。最后,在地垄上挖出一个个小坑,撒上肥料,用浮土盖上,等待扦插薯苗。
这时候,母薯已生出许多嫩芽,长出细细的藤条。人们会将新生的红薯苗用湿润的泥土裹住根部,再用塑料薄膜套住,防止水汽蒸发。这时,全家齐上阵,挑上水桶,拿上镢头、红薯苗,挑上一担水就能种植了。到了地里,先用镢头刨出一个15厘米深的坑,再把红薯苗摁在坑里,用脚踩实,最后浇上水,一棵红薯苗才算种完。第二天,如果感觉坑里的水干了,可以再浇一遍,有条件的,会上些鸡粪或牛粪。
红薯喜温怕冷,初夏温暖的阳光,最适宜薯苗生长,地垄上的红薯一天一个样。为了防止土壤结块,人们经常用锄头将土壤疏松,便于红薯根须向四周蔓延,也有利于茎叶舒张伸展。转眼间,薯苗长成了藤蔓,爬满了地垄,与相邻垄上的藤蔓连在一起。过些时日再去探看,藤蔓愈发粗壮,枝枝叶叶阔大茂盛,它们密密地挨着,一点缝隙都没留,完全看不见叶下的黄土。
一场喜雨过后,站在村头放眼望去,到处绿意盎然。尤其是田野上那一望无际的红薯地,绿油油的一片,像厚厚的地毯,又像绿色的海洋……一行行地垄撑起的,是一层层波浪,令人赏心悦目,沁心爽神。
经过整整一个夏季的阳光照耀、雨露滋润,茂密的青藤下面,红薯尽情汲取光能,吮吸着大地的养分,茁壮成长,日益丰满。
中秋节前后,红薯成熟了。红薯叶开始变黄,人们用镰刀割去盘根错节的藤蔓,发现有的地垄表层已被土里的红薯撑破,形成一道道裂缝。人们用钉耙从地垄沟里开始小心翼翼挖起,当一串串大大小小肉红色的红薯从泥土里翻出来时,是那样令人振奋。刚出土的红薯就像掀起盖头的新娘,羞答答的,它们连根带须,紧紧抱作一团,那是同一个母薯结出的果实。有的红薯扎土很深,起挖时不小心切断了,露出白生生的内瓤,总会令人心里猛地为之一颤,仿佛无意间碰碎了地里的宝藏一般。
割下的藤蔓胡乱地堆放在地头,等闲暇时再作处理,人们一心收拾遍地散落的红薯,除去粘在红薯上的泥土,轻轻地放进箩筐里。刚出土的红薯皮很嫩,要小心别碰破了,否则不利于收藏,更不能留作薯种。
父亲带我去地里起红薯的画面时时在我脑海里浮现。刨出来的红薯装在尼龙袋里,我一趟趟往家背。
红薯挖出后,紧接着就要翻地种小麦了。那时,父亲牵牛犁地时,我会跟在父亲后面,捡拾未挖尽的红薯。脚踩着犁过的沟壑,眼睛紧紧地盯着刚翻的土地,当发现有红薯从土里钻出来时,哪怕是手指头粗细,都像拾到宝一样令人开心。
秋高气爽,家家户户门前院内都晾晒着红薯,有的堆成山,有的铺满地。人们怀着和红薯一样饱满的喜悦心情,对红薯进行整理分类,挑一些大个红薯收藏起来,来年作薯种;又大又好看的,会拿到集市去卖;其余的,或食用,或洗净加工,或留作来年开春后的口粮。
孩子们好奇红薯的千姿百态,将那些造型别致的红薯挑选出来,有的像纺锤,有的像憨态可掬的小鸭子,有的像宝塔一样上尖下圆,有的像人参一般头脚分明。望着造型各异的红薯,怎么忍心吃它?于是,还有人把它们当作工艺品,恭恭敬敬地摆放在堂屋的茶几上,劳动之余,尽情欣赏这些生活中发现的天然之美。
深秋的早晨,我在锅碗瓢盆的交响曲中醒来,母亲早已在厨房忙碌。红薯收获的时节,家家户户都迫不及待地尝食新鲜的红薯。最常见的吃法是“糊”。“糊”红薯,是我们老家一种特殊的蒸煮方式,先将洗净的红薯有序地排列在铁锅里,大火烧热,待嗅到一丝糊香味时,顺着锅盖洒一点热水,烧沸后用小火慢慢地烘焖,直到闻见浓浓的红薯香。当母亲揭开锅时,一团热腾腾香喷喷的雾气顷刻间充满了整个屋子,全家都沉浸在满满的温馨和幸福之中。
食用红薯的花样很多,有时候把红薯洗净削皮后放到稀饭里一起熬煮,稀饭红红的甜甜的,色泽诱人,清香可口;有时候将红薯切成条,放在油锅里煎炸,撒上盐,既可作主食,也可作菜肴;最爱吃的方式,还是放到锅灶底下的炭火堆里焖烤,外焦里嫩,皮黑肉红,香气扑鼻。
冬季来临,气温骤降,红薯怕冻,必须找个恒温的地方保存起来。因此,各家各户都挖有地窖,有的在屋内,从地面垂直向下两三米深;有的在屋外,沿着坎坡横向挖洞,洞口窄窄的,里边越挖越大。储存红薯时,小孩子先进洞,大人们挑选那些没有伤痕的红薯一筐一筐递进去,顺着洞壁一层一层堆好。为了不让冷空气进入,红薯存放好后,还要用稻草或旧棉被将洞口堵得严严实实,外面再砌上土砖密封。全家人从冬到春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些红薯中。
听老一辈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食物匮乏,麦子、玉米满足不了全年的口粮,红薯还一度作为重要的粮食品种,由国家统一收购,调节供求。在春夏之交青黄不接的日子里,红薯常常支撑着老百姓的一日三餐,成为救命粮,养活了数以亿计的百姓。
记得上初中的时候,大部分学生也是带些烤干的红薯片。有时上晚自习饥饿的时候,会拿出整个红薯用小刀切成片,放在火炉上烤。冒着热气的滋味和炉膛里通红的火光成为一道别样的风景。
如今,虽然蔬菜品种很丰富,但百姓餐桌上、宾馆食堂里,红薯依然是人们喜爱的食物。特别是寒冬季节,街上经常能看到推着小车叫卖烤红薯的大爷大妈,远远的就能闻到甜丝丝的红薯香。此时此刻,巨大的诱惑让你忍不住停下脚步。那热乎乎的红薯外焦里嫩,剥开焦硬的外壳,露出橙黄的薯瓤,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顿感香气四溢、暖遍全身、甜沁心头。
我爱红薯,爱它不用种子也发芽的朴实,爱它深藏地下默默无闻的品格,爱它四海为家甘于奉献的精神,就像诗人描述的那样:
红根绿叶垄中生,
从不攀高匍地行。
等到秋来出土后,
香甜美味献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