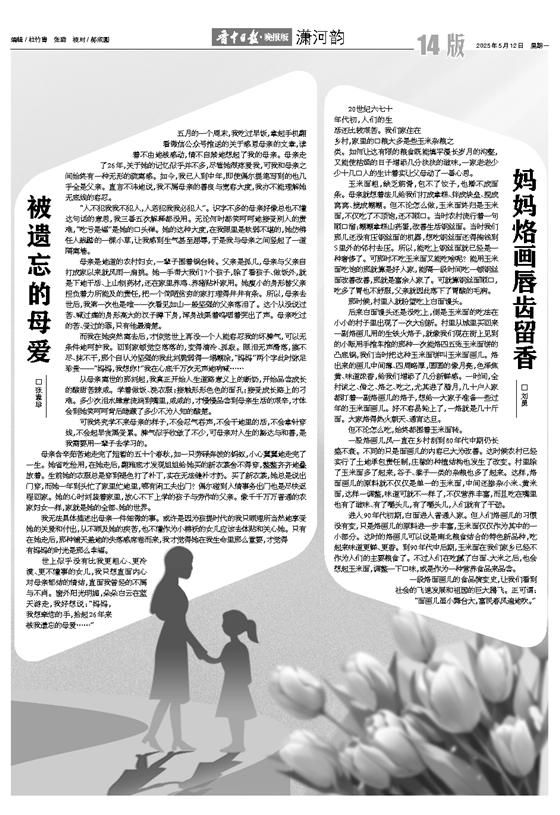妈妈烙画唇齿留香
刘勇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初,人们的生活还比较艰苦。我们家住在乡村,家里的口粮大多是些玉米杂粮之类。如何让这有限的粮食既能填平漫长岁月的沟壑,又能使枯燥的日子增添几分淡淡的滋味,一家老老少少十几口人的生计着实让父母动了一番心思。
玉米面粗,缺乏筋骨,包不了饺子,也擀不成面条。母亲就想着法儿给我们打成拿糕、拌成块垒、捏成窝窝、搅成糊糊。但不论怎么做,玉米面终归是玉米面,不仅吃了不顶饱,还不顺口。当时农村流行着一句顺口溜:糊糊拿糕山药蛋,改善生活钢丝面。当时我们那儿还没有压钢丝面的机器,想吃钢丝面还得掏钱到5里外的邻村去压。所以,能吃上钢丝面就已经是一种奢侈了。可那时不吃玉米面又能吃啥呢?能用玉米面吃饱的那就算是好人家,能隔一段时间吃一顿钢丝面改善改善,那就是富余人家了。可就算钢丝面顺口,吃多了胃也不舒服,父亲就因此落下了胃酸的毛病。
那时候,村里人就盼望吃上白面馒头。
后来白面馒头还是没吃上,倒是玉米面的吃法在小小的村子里出现了一次大创新。村里从城里买回来一副烙画儿用的生铁火烙子,就像我们现在街上见到的小贩用手推车推的那种一次能烙四五张玉米面饼的凸底锅,我们当时把这种玉米面饼叫玉米面画儿。烙出来的画儿中间薄、四周略厚,圆圆的像月亮,色泽焦黄、味道浓香,给我们增添了几分新鲜感。一时间,全村谈之、借之、烙之、吃之,尤其进了腊月,几十户人家都盯着一副烙画儿的烙子,想给一大家子准备一些过年的玉米面画儿。好不容易轮上了,一烙就是几十斤面。大家烙得热火朝天、通宵达旦。
但不论怎么吃,始终都围着玉米面转。
一股烙画儿风一直在乡村刮到80年代中期仍长盛不衰。不同的只是面画儿的内容已大为改善。这时候农村已经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庄稼的种植结构也发生了改变。村里除了玉米面多了起来,谷子、黍子一类的杂粮也多了起来。这样,烙面画儿的原料就不仅仅是单一的玉米面,中间还掺杂小米、黄米面,这样一调整,味道可就不一样了,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吃在嘴里也有了滋味、有了嚼头儿,有了嚼头儿,人们就有了干劲。
进入90年代初期,白面进入普通人家。但人们烙画儿的习惯没有变,只是烙画儿的原料进一步丰富,玉米面仅仅作为其中的一小部分。这时的烙画儿可以说是南北粮食结合的特色新品种,吃起来味道更鲜、更香。到90年代中后期,玉米面在我们家乡已经不作为人们的主要粮食了。不过人们在吃腻了白面、大米之后,也会想起玉米面,调整一下口味,或是作为一种营养食品来品尝。
一段烙面画儿的食品演变史,让我们看到社会的飞速发展和祖国的巨大腾飞。正可谓:“面画儿虽小舞台大,富民春风遍地吹。”